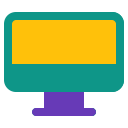保罗·米歇尔·福柯(Paul Michel Foucault,1926-1984年)的哲学家,社会思想家,对1984年去世的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具有深远的影响,在这里,我给您留下最好的用语。
他是监狱或学校等社会机构的一位伟大批评家,提出了``Panopticon''概念,即一种监视系统,其中许多人被看不见的人看到,并在其中执行控制,权力和知识。
您可能也对这些哲学短语感兴趣。
权力无处不在,因为它无处不在。

-我的意思不是说一切都不好,而是一切都很危险,并不完全等于坏。

-灵魂是身体的监狱。

-为什么灯或房屋应该是艺术品,而不是我们的生活?

-我们比我们想象的要自由。

整个社会通过无数的纪律机制迫害每个人。

-知识是不知道的:知识是减少的。

-让我感到惊讶的是,在我们的社会中,艺术已成为仅与物体有关,而与个人或生活无关的事物。

-我认为没有必要确切了解我的身份。生活和工作的主要兴趣是成为一个与刚开始时不同的人。

-有动力的地方就有阻力。

-不要问我我是谁,也不要问我保持不变。无疑有不止一个人像我这样写作,以求没有面子。

-监狱人满为患吗?

-您看到的外观是主导外观。

-panopticon是一种用于分离``看见-被看见''想法的机器:在外围环中,一个人被完全看见,却从未见过; 在中央塔楼,一切都被看到,而从未被看到。

-监狱像工厂,学校,军营,医院一样类似于监狱吗?

-没有知识领域的相关构成,就没有权力关系,也没有没有以权力关系为前提和构成权力关系的任何知识。

-人们可以容忍他们看到一起出去的两个同性恋者,但是第二天他们微笑着,手牵着手,彼此温柔地拥抱在一起,所以不能原谅他们。

-我们的社会不是娱乐社会,而是监视社会。

-知识不是由知识理论决定的,而是由话语实践理论决定的。

-对于纪律处分权,它是通过使其自身不可见来行使的;另一方面,它对提交的人施加了强制性的可见性原则。

死亡离开了它以前的悲剧性天堂,成为人类的抒情核心:他无形的真理,他可见的秘密。
-在一个人说什么和一个人不说之间不做二元划分;我们必须尝试确定不说话的不同方式。
-虚构不是作为对现实的否定或补偿而与现实对立的;它在书本之间,在重复和评论的间隙之间发展;它是天生的,并且在书本之间的间隔中成形。那就是图书馆的现象。
-学校与监狱和精神病院具有相同的社会功能:定义,控制和规范人。
-在您的社会中寻找善良,强大和美丽的事物,并从那里发展。推开自己。始终建立在已有的基础上。然后,您将知道您必须做什么。
-监狱是唯一能以裸露的方式展现自己的力量的唯一场所,它的最大尺度是道德力量。
我不是先知 我的工作是在以前只有墙的地方创建窗户。
我疯狂地爱上了记忆。来自另一个时代和另一个地方的回声。
-身体欠佳的身体会导致ir妄,灰心,不良幽默,疯狂,以至于所获得的知识最终会从灵魂中抛出。
-可见性是一个陷阱。
-既然自然而然地赋予了人类,什么样的欲望可能与自然相反?
现实中有两种乌托邦:享受着从未实现的财产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乌托邦,不幸的是,往往非常频繁地实现的资本主义乌托邦。
- 我不认为一个有悲伤是一个好战,即便真正目的,他是战斗恶劣。
-不要问我是谁,也不要问我要保持不变:让我们的官僚和警察看到我们的文件井井有条。至少我们写作时避免他的道德。
-在没有船只的文明中,梦想破灭,间谍活动取代了冒险,警察取代了海盗。
-关于现代社会的奇特的事情不是他们将性赋予了神秘的存在,而是他们致力于将它性化为无穷大,同时又将它当作秘密加以利用。
-国家要发挥其职能,就必须从男人到女人或从成年人到孩子,建立起具有相对自治权和自身结构的非常具体的统治关系。
-可以说,所有知识都与残酷的基本形式有关。
-自然,只保留了无用的秘密,将人类所必须知道的东西置于人类的触及范围之内。
-在全球范围内,您可能会觉得几乎没有谈论过性。但是,只要看一下建筑设备,纪律法规和整个内部组织就足够了:性总是存在的。
-灵魂是政治解剖学的作用和手段;灵魂是身体的监狱。
-现代社会是不正当的,尽管它有清教徒主义或由于其虚伪而引起的反应;它实际上是直接不正当的。
-犯罪及其寻求的隐蔽特工,以及它所授权的普遍掠夺,构成了对人口进行永久监视的一种手段:一种允许通过犯罪分子自己控制整个社会领域的手段。
-没有一个,但是很多沉默,它们是演说基础和渗透策略的组成部分。
战争不再以必须捍卫的主权者的名义进行;他们是为了所有人的存在而战;为了生活的紧迫性,动员全体人民以大规模屠杀为目的:屠杀已变得至关重要。
-在写作中,重点不是表现或提升写作行为,也不是语言中的固定工具;而是要创建一个作家不断消失的空间。
-一个人要赢得战争,不是因为它是公平的。
疯狂,用它狂野而顽强的词来宣扬它自己的含义;在他的嵌合体中,他说出了他的秘密真相。
-因为有罪的人只是惩罚的目的之一。惩罚首先是针对其他人,完全有罪。
正义必须总是对自己提出质疑,就像社会只能通过它在自身和机构上所做的工作而存在一样。
-发现自由的“启蒙运动”也发明了学科。
政策不是它所声称的那样:集体意志的表达。只有当这种情况变得多重,犹豫,困惑和模糊不清时,政治才能呼吸良好。
当人表现出疯狂的任意性时,他面对世界的黑暗必要性;困扰自己噩梦和被剥夺夜晚的动物是它自己的本性,它将暴露出赤裸裸的地狱的真相。
-工作使我们自己去思考与以前不同的想法。
-精神病学的语言是疯狂原因的独白。
-罚款没有荣耀。
-边缘化的抒情主义可以从暴徒,伟大的社会游牧民族的形象中找到灵感。
-从不给予自我的想法开始,我认为只有一个实际的结果:我们必须将自己创造为一件艺术品。
-我正在寻找的是永久性开放的可能性。
-无论如何,可以肯定的是:人类既不是人类知识提出的最古老也不是最永恒的问题。
-“代表”或“反对”理性,真理或知识是没有意义的。
-只有在隐瞒其中相当一部分的情况下,才能接受委托书。它的成功与它隐藏自身机制的能力成正比。
-在权力机制中,已对不便之处进行了战略性利用。监狱创造了罪犯,但罪犯最终在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有用。罪犯服务。
-有关监狱的公开信息很少,它是我们社会系统中的隐蔽地区之一,是我们生活中最黑暗的地区之一。
-有些形式的压迫和统治变得看不见,其中之一就是新常态。
-知识不是人性的一部分。冲突是战斗的结果,也是偶然的结果,是引起知识的原因。
-正如思想考古学先前所表明的,人是最近的发明。
-良心自由比权威和专制主义承担更多的危险。
-不应用仪器或机构来识别学科。这是一种力量,可以让您压缩一组乐器。
-事实可以理解为一种有序程序的系统,其目的是产生,调节,分发和操作报表。
-成功总是与掩饰自己机制的能力成正比。
-只要我们不知道结局是什么,游戏就值得。
我与人的关系就像一个演员。当我说完之后,我会感到完全孤独。
-酸性蒸气不具有与忧郁症相同的特性,而含酒精的蒸气总是随时准备着火并表现出狂热。
-关于监狱的迷人之处在于,权力通常不会被掩盖或掩盖,而是在暴政紧随其后的情况下展现出来的,即使是最小的细节。
-写作与死亡之间的关系反映在写作主体个人特征的淡入中。
-作家的商标仅受缺席情况的影响。
-人类的生命以永远不在正确位置的依赖生物结束。最终注定会游荡并犯下无尽错误的生物。
-从基督徒的角度来看,人的理性比上帝的理性疯狂。但是,神圣的理性似乎是出于人类理性的疯狂。
-在17世纪的社会中,国王的尸体是政治现实中的隐喻。国王的身临其境对于君主制的运作至关重要。
-我相信,由遗嘱的普遍性构成的尸体的社会思想是一种巨大的幻想。
-只有通过体内力量的作用和转化,才能获得对自己身体的掌握和充分的意识。
-有些邪恶的外墙具有强大的传染力,这种丑闻势力使任何宣传都会使它们无限繁殖。
-孤立无缘无故地被掩盖,背叛了它所引起的耻辱,并明确提请人们注意疯狂。
-疯狂反映了动物性的秘密,无非是它本身的真理,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它吸收了许多目的。
-差异仅在恐惧不再被用作停止运动的方法并被用作惩罚的那天才开始以其全部强度开始存在。
-来自他自身的唤醒,以及它在疯狂的环境中坚持不懈的,必不可少的进步,唤醒了他面对的真理,但速度较慢,但更加确定。
-地球上有比学术界想象的想法更多的想法,而且这些想法比政客们的想法更活跃,更坚强,更有抵抗力和更热情。
-不应在中心的主要存在或单一主权空间中寻求权力最终的条件。
-权力无处不在,并不意味着它吞没了一切,而是无处不在。
-权力关系分析是一个复杂的领域。有时会遇到统治状态和状态,而不是移动,而是让参与者采用修改它们的策略。
-行使权力会创造和发芽新的知识对象,从而可以积累新的信息体系。
-权力不断问问题并不断问我们,查询和注册;它使对真理的搜寻制度化,使其专业化并最终获得回报。
-真理的话语决定了一部分,因为它传播并促进了权力产生的影响。
-他们不会惩罚同样的罪行,他们不会惩罚同样的罪犯。但是它们很好地定义了每一种特定的刑罚风格。
-权力是在网络中行使的,个人不仅在其中流通,而且总是处于遭受和行使的位置。
-个人是权力的一种影响,同时在某种程度上是权力的救济:权力通过权力所构成的个体。
-现在,公共处决被视为恢复暴力的焦点。
-值得惩罚是丑陋的,但惩罚不光彩。
-身体上的痛苦,即身体本身的痛苦,不再是惩罚的构成要素。惩罚已经从一种令人难以忍受的感觉艺术转变为一种停权的经济。
-惩罚性司法手段现在必须咬合这个无形的现实。
-权力不会停止质疑,质疑我们;他不停止调查,登记;使对真理的搜寻制度化,使其专业化,对其进行奖励。